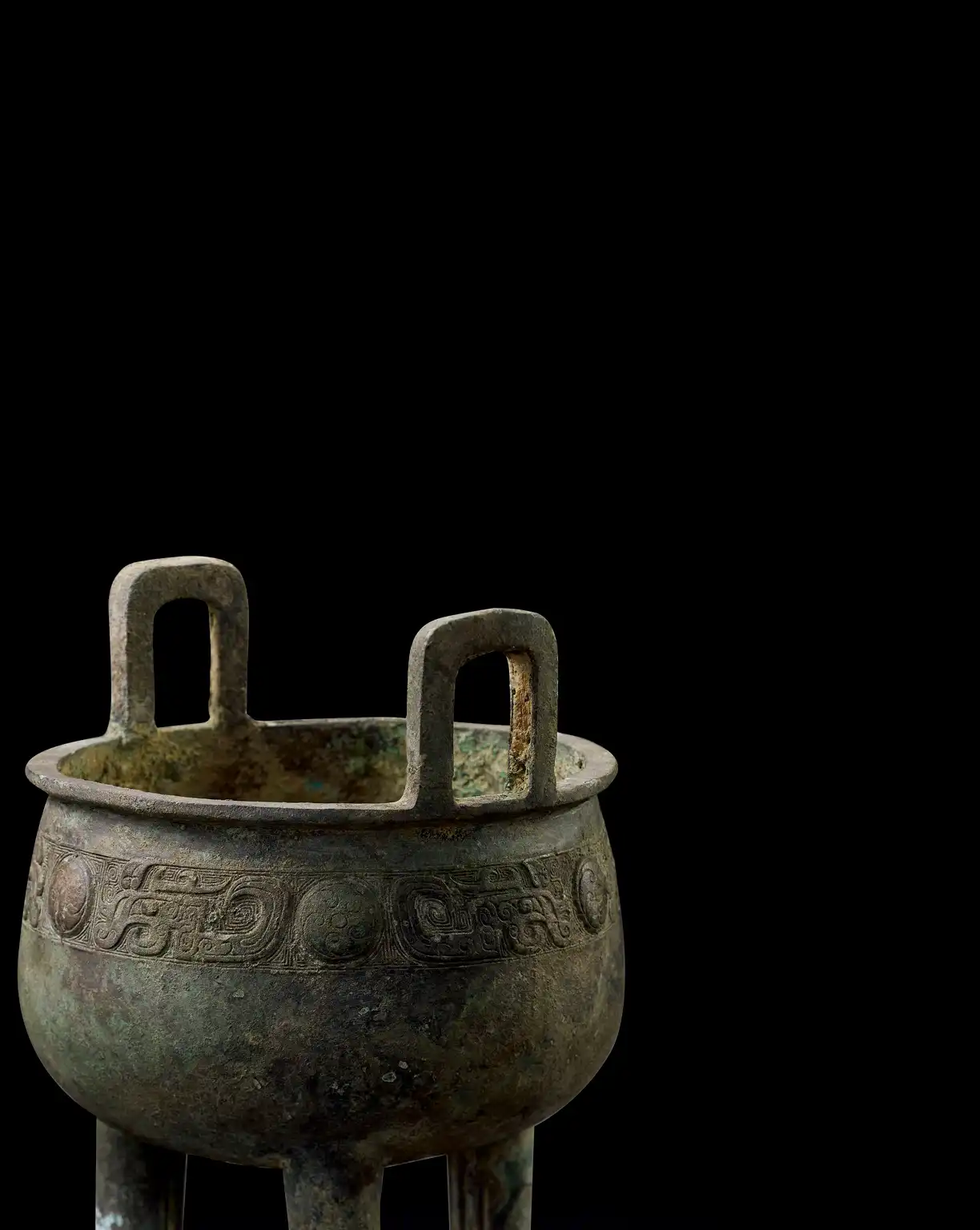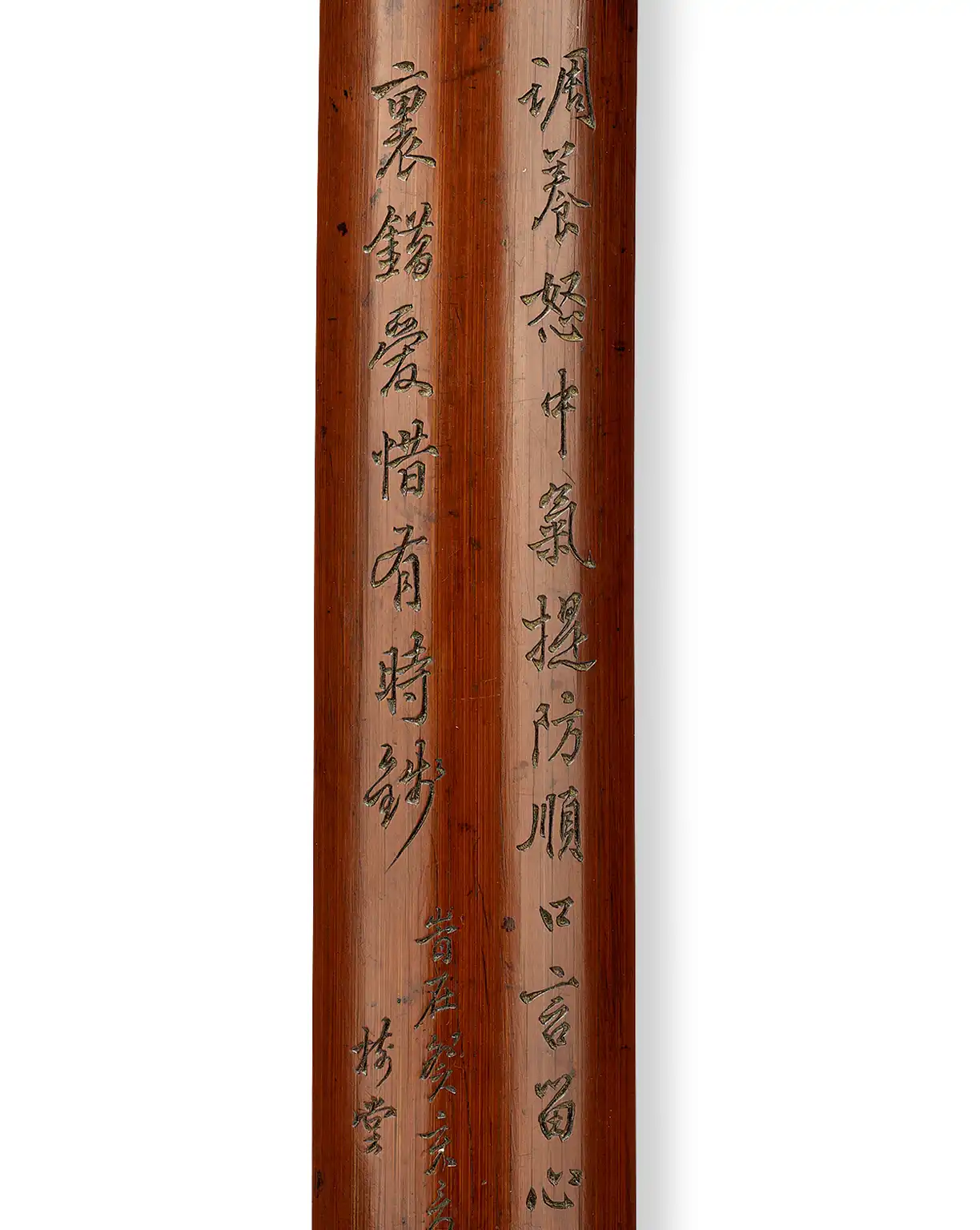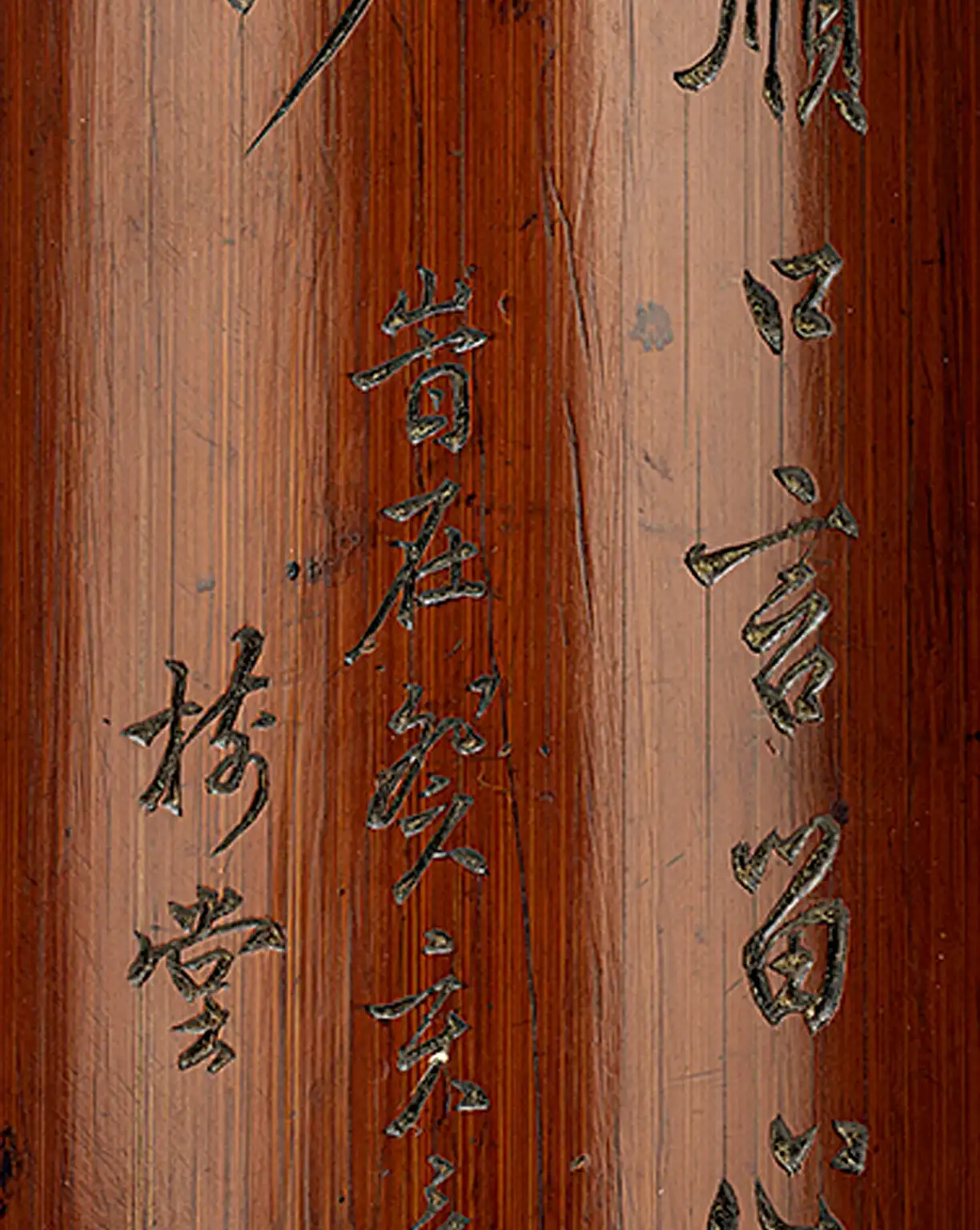華年繁珍 50-60年代 日、港、台資深藏家珍藏專場
4048 唐代 金伎樂紋八稜杯一對
A PAIR OF GOLD OCTAGON CUPS WITH DANCER MOTIF Tang Dynasty
起拍價: NT$500.000
H 6.5cm
金質八稜杯二件,外觀幾同,可稱一對。皆屬完存,麗澤仍盈溢於表。敞口,壁微弧分八面,收直於腹,底面略窪,下衍撇圈足,並沿一稜半高處加正圓提耳,上蓋指墊。器外紋飾華滿,通體填魚子地紋,器側出稜界,每面各施浮雕一人,服裝、樣貌皆異:其中二人戴圓帽,餘六人則頂尖帽,兩人手捧壺、杯,四人分持不同樂器,八位歌者、舞者及樂工共同組成伎樂班隊;又於其周圍和指墊焊陽線花卉、蔓草紋,並在足緣綴連珠一圈。工技複雜,構思巧妙,尚相攜成對,唐風富麗,甚加難得。 唐代是中國史上金銀藝術最發達的時期,其原因不外乎國力強盛和東、西的頻繁往來。按唐代金銀器最初由宮廷壟斷,生產過程相當系統化,除包辦採礦至加工全程,亦不以成本為憂,且有相當嚴謹的選材與監工制度,令金匠一職往往世代相傳;同時,當時盛行地方官進奉禮品至宮廷之風習,也促進了地方官辦作坊與民間工匠二者在中唐以後興起[1],遂留下今日所見的龐大成就。 此外,唐代之所以能在金工方面創下極高造詣,也和外國金銀器大量傳入中土帶來的啟發脫不了關係,例如此器一類的八稜單耳杯顯然是基於粟特式銀杯的產物:按七世紀後半起阿拉伯帝國(大食)透過戰爭向東擴張,使得原本居住在中亞的粟特諸國為躲避戰亂、尋求復國而大舉遷入唐域[2]。除釀酒技術外,粟特器物中對唐影響最大者便屬金銀器,當時有些移民甚至在如揚州一類的大城市作坊中直接參與生產[3]。考八稜杯原本僅有銀質[4],而在中原金匠發揮之下有了純金和銀鎏金之例,還多能結合纏枝花卉紋和伎樂紋等同樣富異域風情的裝飾,使得這種器形於唐代金銀器中獨出一格,甚至受契丹民族承繼。迄今發現的唐代八稜杯極少,與此器同屬金質且飾伎樂紋的出土同形器概有三例,包括何家村窖藏二件(參閱1、2)和黑石號沈船一件(參閱3)——前者的埋藏時間或為涇原兵變爆發時(783年),或許是被官員緊急攜出的皇室財物[5],後者則依沈船同位素檢測被歸於九世紀前葉(見參閱3),並被認為可能是成於粟特工匠之手的客製外銷品[6]——此器的體積、細節與何家村遺存較近,而二發掘例的年代未相去甚遠,皆可為進階考究之依據。 註腳 [1]齊東方:《唐代金銀器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頁268-293。 [2]李樹輝:〈唐代粟特人移民聚落形成原因考〉,《西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2期,頁14-19。 [3]齊東方:〈唐代粟特式金銀器研究——以金銀帶把杯為中心〉,《考古學報》1988年第2期,頁154。 [4]齊東方:〈“黑石號”沈船出水器物雜考〉,《故宮博物院院刊》2017年第3期(總第191期),頁15-17。 [5]齊東方:〈何家村遺寶的埋藏地點和年代〉,陝西歷史博物館:《花舞大唐春:何家村遺寶精粹》(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頁13-16。 [6]顏雙爽:〈入華粟特工匠與唐代金銀器——從“黑石號”八棱金杯說起〉,《美術教育研究》2021年第9期,頁44-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