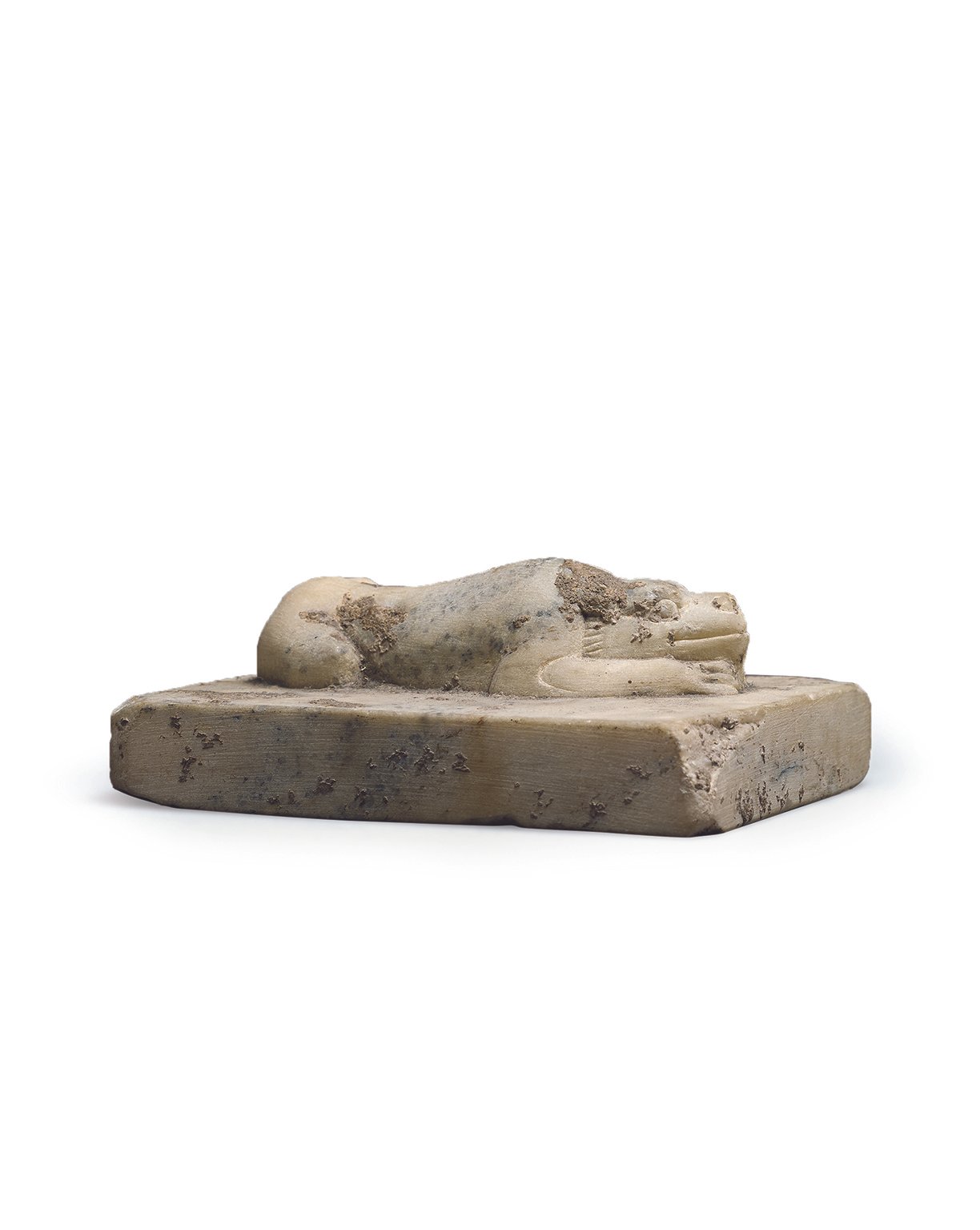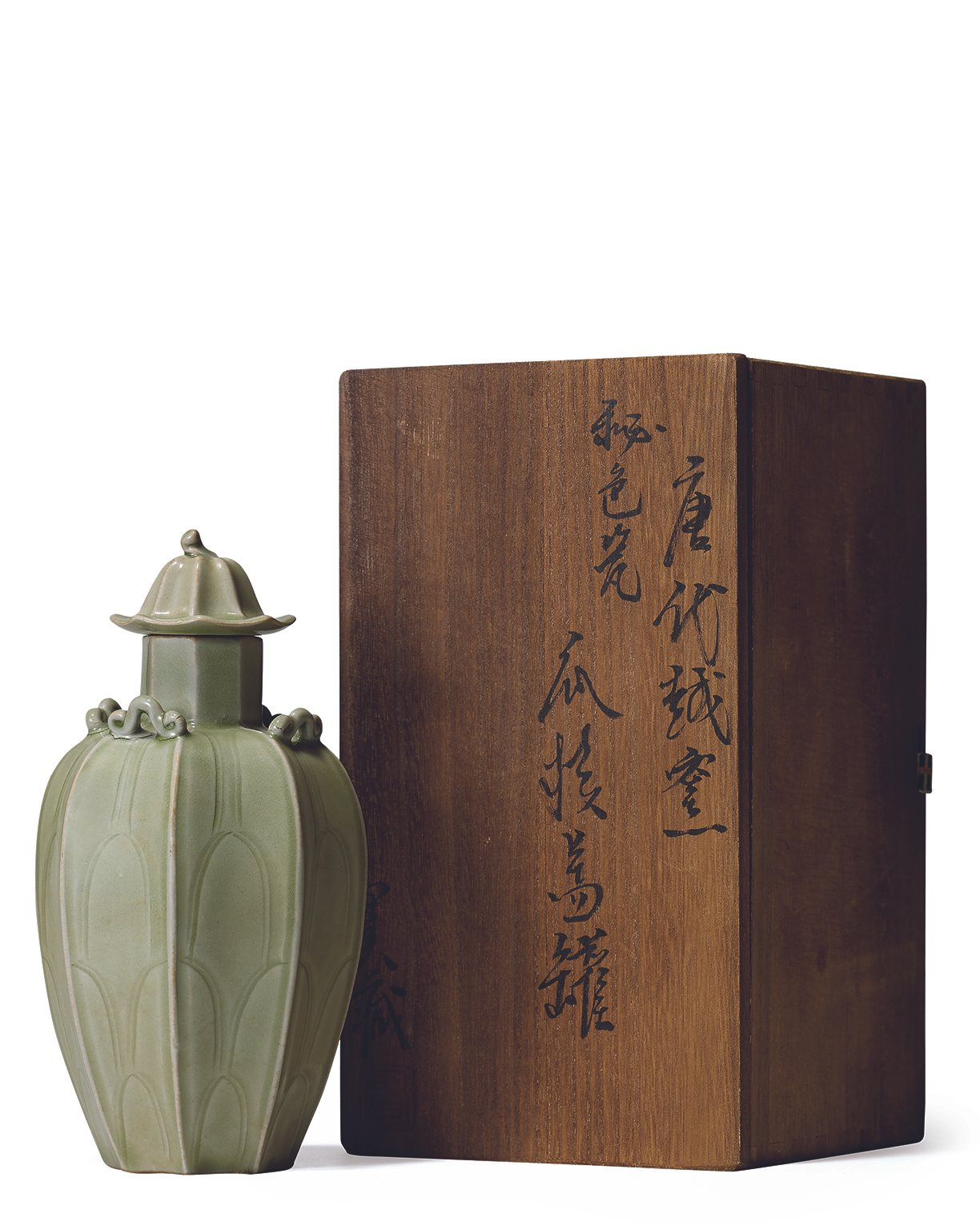50-70年代 日本、香港資深藏家珍藏專場
7015 秦/漢 銅錯金銀仙人騎鶴香熏
GOLD AND SILVER INLAID BRONZE INCENSE PARFUMIER WITH DEPICTINGIMMORTAL RIDING CRANE Qing/Han Dynasty
起拍價: NT$400.000
H 16cm
全器以青銅鑄成,再施以錯金銀。此香熏以展喙仙鶴為座,背負一高冠長鬚仙人,仙人面相寫實,鬚髯及五官刻劃生動,雙手作持物姿,一手持書簡,另一手持寶扇,全器通體以細密漩渦紋與鱗羽紋裝飾,採錯銀輔以局部錯金點綴,鶴翼羽片以V形平行刻線表現,細緻入微,鶴背開置香艙,置香後煙氣由頸部導向喙部吐出,寓意祥雲繚繞,乘鶴升仙,綜觀此器,仙人與鶴皆寓長生、清高之意,「乘鶴」為成仙升舉之象徵,為秦漢方士及求仙文化流行的標誌圖式,常見於銅熏、博山爐、帶鉤或鏡背等。
此件以青銅為底,表面精細地錯以金銀,工藝繁複且華美,主體為一隻昂首的仙鶴,羽翼間錯落金銀線條,鶴背上端坐一位神態自若的仙人,身穿寬袍,形象端莊祥和,展現「乘鶴升天」的仙道理念。據《雀豹古今注》記載:「鶴千年則變成蒼,又兩千歲則變黑,所謂玄鶴也。」所以鶴寓意著長壽,並被賦予忠貞清正、品德高尚的文化內涵,在中國傳統吉祥圖案裡十分常見,有鶴鹿同春、松鶴長春、松鶴延年等多樣變化。秦始皇陵銅禽坑是位於陜西省西安市臨潼區晏寨鄉孫馬村的秦代陪葬坑遺址,距離秦始皇陵中心約1.5公里,為已發現距離陵墓最遠的陪葬坑。該遺址於2000年8月由村民發現線索後,經陜西省考古研究所與秦俑博物館聯合勘探確認。考古工作者在七號坑共清理出土青銅禽46件,其中銅鶴6件,天鵝20件,其它為鴻雁等禽類。這些青銅禽都與實際大小相同,動作姿態多種多樣,個別銅禽身體上能看到清晰的彩繪痕跡,這些水禽分布在一條模擬小河兩岸的台地上,有的在覓食,有的在小憩,動作各異,但頭部都面向中間的河道。其中有一隻青銅鶴,被學者認為是出土禽類中最為引人注目的一個,它長喙,曲頸,羽翼豐滿且雙腿修長,嘴里銜著青銅製成的小魚,捕食姿態十分生動,從鶴身上栩栩如生的羽毛到只需兩隻細長鶴腳便能成功撐起沈重的青銅鶴身,這些工藝技巧無不讓現代人對秦代工藝師的高超技術嘆為觀止,此外,在青銅鶴的底座上,裝飾著秦漢時期流行的雲紋,表明這隻鶴正停駐在白雲之巔,是為「仙鶴」。據史籍記載,秦始皇癡迷於長生不老,曾派遣大批方士出海尋覓不死藥,秦始皇使用青銅仙鶴作為陪葬品,箇中緣由正是他期盼能借鶴為輿,騰雲升天,以圓生時長壽、死後成仙的美夢,換言之,這隻青銅鶴的出土,成為秦始皇「仙人夢」最生動的實物論證。
北京故宮博物院庋藏春秋時期的〈蓮鶴方壺〉或可作本件另一參照,該壺為酒器,方壺分為三部分,壺蓋、壺身和壺座。壺身的表面為十字纏繞的蟠螭紋和鳥紋,壺四面鑲嵌四隻鏤空雙角龍壺耳,四角有四隻帶翅膀小龍。底座用兩隻卷尾龍撐起整個方壺。最為精彩的是壺蓋,壺蓋四周蟠螭紋纏繞,頂部雙層盛開狀蓮瓣,烘托一隻展翅欲飛的仙鶴,仙鶴下面是一個單獨的小蓋。青銅器作為祭祀重器,荷花與仙鶴的出現,打破過往沈重肅穆的氛圍,為方壺注入了新的活力。
錯金銀是中國古代青銅器及玉器上的一種精細裝飾工藝,指在器物表面刻出凹槽或紋飾後,鑲嵌金絲和銀絲的技法[註1]。這種工藝起源於東周時期,在漢代達到鼎盛,並在玉器上也有廣泛應用。錯金銀工藝不僅表現出華麗的裝飾效果,也象徵了當時貴族和權貴的身份與財富。漢代錯金銀工藝技術成熟,塑造出諸多精美珍品,不只反映了當時社會的科技水平與美學追求,還通過絲綢之路傳播至中亞及北印度,對中外文化交流產生深遠影響。
而博山爐是漢代極負代表性的香熏器物,「博山」意指東海蓬萊、方丈、瀛洲三仙山,其蓋形層巒疊嶂,鏤孔隱約如山巒雲氣,往往置於宮廷或貴族府第中央,焚香時煙雲繞繞,似神話仙山,給人無限的想像空間,既呼應「仙山」意象,也方便人對神明、祖先實行祭祀與祈福。漢代博山爐作為香薰之器在功能上有多重用途,除淨化空氣、薰衣除穢和取暖外,亦因神仙信仰而富有象徵意義。若比較本件與博山爐之間的異同,仙人騎鶴香熏更偏重於立體人物與仙禽的生動表現,主題鮮明且直接象徵「乘鶴升天、得道長生」,突出「仙由人變」的神仙觀念,博山爐則以裝飾性構建出神山、仙島和煙雲繚繞的仙境氛圍,將對神仙世界的想像融入日常生活的香薰用具中。兩者均是漢代仙人思想器物化與圖像化的代表,只是一個側重在個體仙人塑像,一個側重在集體仙境的營造,對於我們了解漢代仙人思想及工藝技法提供了良好線索。
註腳
[1]童宇:〈再論錯金銀〉,《故宮文物月刊》第425期,(臺北市:國立故宮博物院,2018年),頁106-113。